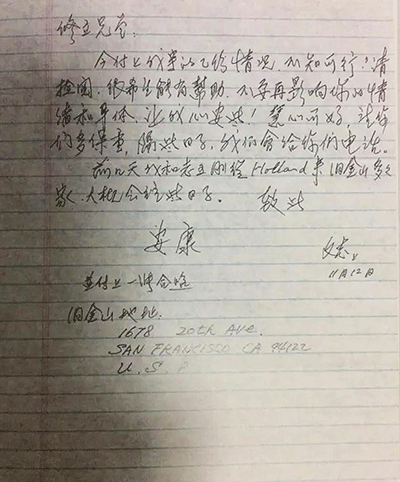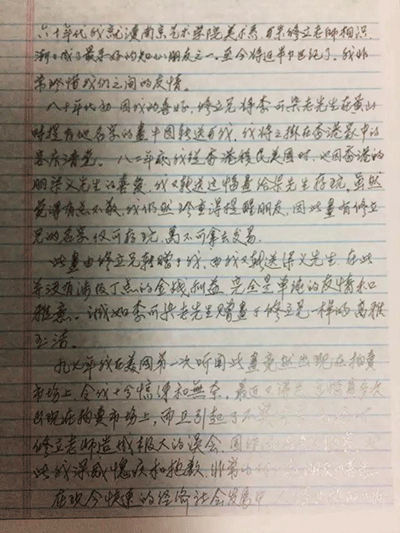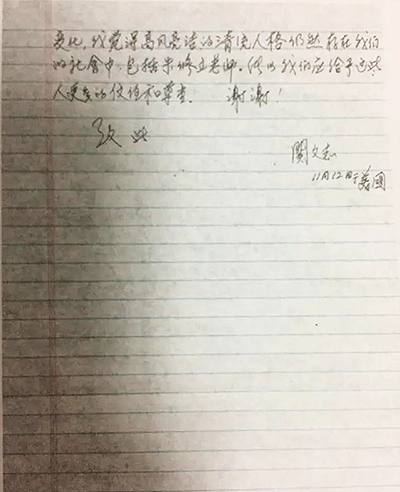上文完成后,未能找到发表的机会,2006年,我搬到北京去住,在一次展览会的开幕式上,我见到了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老师。老人身体健康,精神很好,我们一起照了相。接着邹老师问我,“李老师给你的画还在吗?”我很意外这个问题。原来,李老师临行时,送了一张四尺三开《牧童与水牛》的画给我留念,我爱如珍宝,是年1978年六月。第二年,原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位华侨学生来向我告辞,说公安局终于批准他出国定居。临行,他希望我留一件纪念品给他,当时穷得一无所有的我,唯一值得珍藏的只有可染先生的这幅画,便忍痛转送给了他,并在画的左方中间,题上“转送给关文志同学”的字样。
为什么我要把珍爱的东西送人?这需要说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。1960年印度尼西亚与我国的关系正处于“蜜月期”,印尼共产党书记艾地发动突然政变,企图推翻苏加诺政府而遭到了失败,印尼政府大肆镇压、捕人。(阅读原文为印尼撤侨事件)一大批印尼共产党及外围组织、华侨同胞卷入其中。我国政府只得接受了一批流亡的华侨子弟。关文志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南京读完中学,又被安排在南艺学艺术,接着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。社会一片动乱。校内外造反派文武齐下,斗领导和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受到冲击很大,有的人受不了羞辱和身体上的摧残而选择了自尽。在这种情况下,关文志由于身份特殊,同情并保护了不少老教授,所以我对他有好感,很信任,在一片极左、高压恐怖的年代,相互间都不敢有任何心灵的交流,而我们之间的这种信任,使师生关系演变成了师友关系。当他获准离开这是非之地时,我将心爱之物送给他作纪念应属可以理解之事。文革结束才不久,极左的思潮,仍然十分盛行,他这一去,几乎便是“生离死别”。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他先去了香港,而后去了哪里,我一无所知;我也由南京艺术学院调到安徽六安师专工作,又被调到安徽省书画院,彼此之间失去联系。相隔十七年后的一天,画院电话通知我,有一封国外的来信,竟意外地收到他来自美国的消息。原来,他在美国书市上看到我出版的荣宝斋画谱,获悉我在安徽省书画院工作,这才取得联系。1997年,我出访美国、专程去了他家,老友相聚,欣喜异常,相互关心分手后的种种。他初到香港时,人地生疏,不得已住在商人梁某家中,并得到他的帮助。后来获准去美国与丈人—家团聚。离开了梁某,临行时,梁某要他这张李可染先生的画,这幅画便到了梁的手中。
这一切是我听到邹老师问话之后去追问下落时,才弄明白。当邹老师告诉我说这幅画现在国内市场拍卖,我十分惊愕,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连关文志也出乎意外。因为他认为梁老板本来很有钱,大可不必去卖这幅画。由于我的追问,才弄清这一事情的始末。2011年,我朋友告诉我,此画又在杭州拍卖会上出现了,定价为80万,我朋友带了120万准备把画拍回来,结果卖家见有人追拍,一路抬升,直到240万还不罢手,我朋友只得放弃。我也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去摆平这事,现在我只能请关先生把事情原委写信说明,我去向邹老师请罪,一方面,对邹老师的关切有一个交代,也是我心理负疚的解脱。
如今邹老师已年过九十,我也过了七十五岁,又有了病,希望在有生之年清除我心理的阴影,希望可染老师在天之灵得到抚慰,邹老师健康、长寿。写下这一段“故事”,也算是“艺坛逸事”,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,令人感慨!
愿天下从此太平,少生离乱。
(朱修立写于2013年。 时下邹佩珠先生98岁、朱修立先生80岁)
关文志先生手稿如下图: